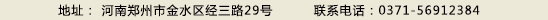ldquo行气或可以治百病,或可以
现代预防医学认为传染病(古时泛称瘟疫)是由病原体引起,能在生物体之间传播的多种疾病的总称。传染病流行要求必须同时具备传染源、传播途径和易感人群三个基本环节。因此,传染病的预防措施以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和保护易感者为主要内容。
中国汉朝开始,道教就认识到瘟疫是瘟鬼施放的毒气,认为感染毒气的原因既可能是善恶报应、承负灾祸也可能是身体缺乏保养、元神不固。基于道教对瘟疫致病原因的分析,道教一方面主张通过原始巫术式的恫吓、以忏悔谢罪为主的祈禳之术和具有象征意蕴的送瘟仪式等道教法术来治瘟,另一方面也强调通过施药、存想、行气等道教医术来治瘟。道教治瘟的思想基础主要包括道生万物的宇宙论、形神相依的人体观、天道承负的伦理观三个方面。道教治瘟对中国古代社会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瘟疫在古代社会具有极大的破坏性,而道教正诞生于汉末瘟疫多发之时,其创教即与瘟疫治疗的实践产生了紧密联系。道教对瘟疫产生的原因依自身宗教义理给出了独特的解释,并提供了多样化的治疗方法。中医方剂、道符、咒语和斋醮科仪属于信仰疗法、心理疗法的范畴,而道教防治瘟疫的养生术则具有一定的科学依据,在今天仍有重要的价值。
传染源指的是体内有病原体生长、繁殖并且能排除病原体的人和动物。现代防疫思想指出,针对不同传染源可采取不同的控制措施,如对病人可采取隔离法,这在古代社会就已施用。此外,道教对动物传染源也提出了控制措施。
1.隔离法
隔离法,是指将传染病病人或疑似者安置在一定场所,使之不得与易感人群接触的措施,其方式根据疾病的传播途径因时因地而定。
东晋道士葛洪著《肘后备急方》,古代中医方剂著作。是中国第一部临床急救手册。中医治疗学专著。8卷,70篇。东晋时期葛洪①著。原名《肘后救卒方》,简称《肘后方》。系作者将其原著《玉函方》(共卷),摘录其中可供急救医疗、实用有效的单验方及简要灸法汇编而成。经梁代陶弘景②增补录方首,改名《补阙肘后百一方》。此后又经金代杨用道摘取《证类本草》中的单方作为附方,名《附广肘后方》,即现存《肘后备急方》,简称《肘后方》。
注释①:葛洪字稚川,江苏句容人,约生活于公元3-4世纪,享年81岁。其父、祖父都是大官僚,其本人也因参加过镇压农民起义而被赐爵关内侯。晚年隐居于广东罗浮山修行,“欲炼丹以祈遐寿”,“优游闲养,著述不辍”,直至去世。
注释②:陶弘景(公元—年),字通明,南朝梁时丹阳秣陵(今江苏镇江一带)人,号华阳隐居(自号华阳隐居)。著名的医药家、炼丹家、文学家,人称“山中宰相”。作品有《本草经注》、《集金丹黄白方》、《二牛图》、《华阳陶隐居集》等。
陶弘景的一生,跨宋、齐、梁三代,经历可谓复杂。虽然梁武帝对其恩遇有加,《南史》也有“山中宰相”之誉。但在南梁时期,举国崇佛的大环境下,陶弘景作为道教茅山派代表人物,迫于压力出走远游。最后以道教上清派宗师的身份,前往鄮县礼阿育王塔,自誓受戒,佛道兼修。正是如此才避免了如寇谦之的新天师道一世而亡的下场。
后人皆将此事视作齐梁佛道交融的例证来宣讲,却从未分析陶弘景礼佛的真实原因。陶弘景此举,实非出于自愿,而是为维护茅山道众的生存不得已而为之。陶弘景有悼好友沈约诗云:“我有数行泪,不落十余年,今日为君尽,并洒秋风前。”
陶弘景被迫受戒后,假借悼念沈约之实,诉说自己痛苦之心境。苏东坡所感慨的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实古今皆然,博大如陶弘景者也概莫能外。陶弘景工草隶行书尤妙。对历算、地理、医药等都有一定研究。曾整理古代的《神农本草经》,并增收魏晋间名医所用新药,成《本草经集注》七卷,共载药物种,并首创沿用至今的药物分类方法,以玉石、草木、虫、兽、果、菜、米实分类,对本草学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原书已佚,现在敦煌发现残本)其内容为历代本草书籍收载,得以流传。
《黄帝内经》提出对瘟疫要注意“避其毒气”,与现代预防医学的隔离思想契合。据《蜀记》记载,张道陵因患疟疾而到神社中“避病疟”,曰:“张陵避病疟于丘社中,得咒鬼之术书,为是遂解使鬼法。”《肘后备急方》也提到将麻风病患者送入深山进行隔离的方法,曰:“余又闻上党有赵瞿者,病癞历年,众治之不愈,垂死。或云不如及活流弃之,后子孙转相注易,其家乃赉粮,将之送置山穴中。”当时社会认为瘟疫多是鬼神所致,因此便有“避疾”的方法,使患者远离人群,隔绝了传染源。
此外,道教还用“隔断”法术禁断瘟疫传染。该法术引导信众有意识地规避传染源,提升信众的自我保护意识。《道法会元》记载宋元时期的“隔瘟法”:“凡邻家有时灾,恐不知忌炁息传染者,须当择一日,奏申行移如意,书篆符命镇断……望病人家向浇画地界,用画河开五路九宫断法禁之,牒檄官将守卫,再以和瘟符烧於灶中及池井水缸等处。”向病人家室“浇画地界”,用“断法禁之”,禁止未患病者进入病人家的地界,从而隔离传染源,故“隔断”法术可认为是隔离法的形式之一。
2.控制动物传染源
动物传染源可作为某些病原体的宿主,使得疾病在动物和人之间互相传播,因此不能忽视动物传染源。
葛洪指出,对于经济价值较大的动物传染源,如牛马等牲畜,可采用赤散方予以治疗。曰:“牛马疫,以一匕著舌下,溺灌,日三四度,甚妙也。”还指出狂犬发病的征兆:“及寻常忽鼻头燥,眼赤不食,避人藏身,皆欲发狂。”并指出控制狂犬的方法:“宜枸杞汁,煮糜饲之,即不狂。”孙思邈也明确指出控制狂犬的方法:“凡春末夏初,犬多发狂,必诫小弱持杖以预防之。”
葛洪还指出“射工毒”和“沙虱毒”动物宿主的控制方法:“当养鹅鸭,食,人行将纯白鹅以辟之,白鸭亦善。带好生犀角,佳也。生麝香、大蒜合捣,以羊脂和,著小筒子中,带之行。”即对于“射工毒”,可通过饲养鸭鹅来捕食射工毒虫的方法,或者佩带生犀角躲避射工毒虫的方法控制毒虫侵袭;对于“沙虱毒”,可利用麝香和大蒜避免沙虱近身。
切断传播途径:传播途径是指病原体从传染源到易感人群的传播过程,常见的传播途径有:水、土壤、空气、飞沫、经节肢虫类传播等。消毒是最常用的切断传播途径的措施,道教对此做出了诸多实践。
1.消毒法
消毒法是道教常用的防疫手段,包括烧熏、佩挂和涂抹药物消毒法。这类药物多以雄黄等本草香物为主,其药物本身、烧熏气体及挥发油成分均具有一定的消毒灭菌作用,从而发挥卫生防疫功效。
烧熏消毒法利用消毒药品的燃烧所产生的气体进行空间消毒,一般在院内、中庭烧之,通过燃烧熏蒸方式达到消毒空气环境的作用。《肘后备急方》记载诸多烧熏法的辟瘟疫方,如“太乙流金方……中庭烧,温病人亦烧熏之”和“虎头杀鬼方……每月初一、十五半夜院内烧一丸”。《备急千金要方》亦记载诸多烧熏辟瘟疫方,如太一流金散方③、杀鬼烧药方④、虎头杀鬼丸方⑤、辟温杀鬼丸和雄黄丸方⑥等。将这类中药焚烧后熏蒸庭院,起到对居住环境的消毒作用,一定程度上切断病原体的传播。
注释③:《太一流金散》(《千金》卷九)、雄黄散(《圣惠》卷十六)、流金散(《圣济总录》卷三十三)。本方方名,《外台》引作“太乙流金散”。方中“羖羊角”,《外台》作“羚羊角”。药物组成:雄黄3两,雌黄2两,矾石1两半,鬼箭1两半,羖羊角2两。
注释④:《杀鬼烧药方》是一种药物,主治妇人与鬼交通。出自《千金》卷九。雄黄1斤,丹砂1斤,雌黄1斤,羚羊角(羖羊角亦得)3两,芜荑3两,虎骨3两,鬼臼3两,鬼箭羽3两,野丈人3两,石长生3两,(豕段)猪屎3两,马悬蹄3两,青羊脂8两,菖蒲8两,白术8两,蜜蜡8斤。上为末,以蜜蜡和为丸,如弹许大。朝暮及夜中,户前微火烧之。
注释⑤:《虎头杀鬼药方》虎头杀鬼丸、杀鬼虎头丸、虎头丸、七物虎头丸、虎杖头杀鬼丸、辟瘟杀鬼丸
虎头骨5两,朱砂1两半,雄黄1两半,雌黄1两半,鬼臼1两,皂荚1两,芜荑1两(一方有菖蒲、黎芦,无虎头、鬼臼、皂荚)。
上为末,蜡蜜为丸,如弹丸大,绛囊贮之。
辟温。除一切疫气。主
虎头杀鬼丸(《千金》卷九)、杀鬼虎头丸(《圣惠》卷十六)、虎头丸(《医方类聚》卷五十八引《澹寮》)、七物虎头丸(《东医宝鉴·杂病篇》卷七引《宝鉴》)、虎杖头杀鬼丸(《普济方》卷一五一)、辟瘟杀鬼丸(《兰台轨范》卷七)。《医方类聚》引《澹寮》本方用法:晨起各人吞小豆大一丸,不致传染。
《肘后方》卷二:看了上面文章关于虎头杀鬼方的介绍,我突然发现好的身体还是要从饮食做起。平时大鱼大肉和太寡淡都不是养生之道,科学的荤素搭配才是最重要的。
注释⑥:《雄黄丸方》主治疔肿,小儿中恶心痛,小儿诸般喘嗽,盐醋等齁哮吼,时气热毒,下痢赤白;及下部毒气,下细虫如布丝,长四五寸,黑头锐尾;蛊注;四肢浮肿,肌肤消索,咳逆腹大如水状,漏泄,死后注易家人,食蟹中毒,烦乱欲死者。
佩挂药物法利用药物的挥发性,将其气味持续释放而防御疫邪侵袭,至今仍然在民间使用,佩挂部位一般是床帐前、门户上、胸前、手臂等。《神仙传》记载道士尹轨⑦擅长通过佩挂“辟疫药丸”的方法预防瘟疫的事迹:“尹轨者……腰中带漆竹管数十枚,中皆有药,入口即活,天下大疫,有得药如涂其门,则一家不病,病者立愈。”《肘后备急方》强调通过佩挂药物法可有辟瘟疫的良效,曰:“有辟瘟疫的单行方术……悬门户上,又人人带之。”此外,对于预防蛊毒也采用佩挂药物法,曰:“得真犀、麝香、雄黄为良药,人带此于身,亦预防之。”《备急千金要方》亦记载佩挂药物防疫法的相关要方,如太一流金散方、虎头杀鬼丸方、辟温杀鬼丸、雄黄丸方和赤散方等。
注释⑦:尹轨字公度,山西太原人。他精通《诗经》、《尚书》、《礼》、《易》、《春秋》这五经,尤其擅长天文星象和河洛图解方面的学问。晚年他专心学道。经常服用黄精粉,每天服三盒,已经活了上百岁。他常常预言天下的兴盛或衰亡,别人的安危吉凶,都非常灵验。尹轨平时腰里挂着十几个上了漆的小竹筒,里面全装的药,他说他的药可以使人免受兵祸和瘟疫之灾。有一次他给人一丸,让那人把药带在身上。当时世道很乱,那人的乡亲都遭到了祸事,只有那人免除了祸患。瘟疫流行时,如果能把尹轨的药一小粒涂在门上,全家就不会被传染上瘟疫。他有个弟子叫黄理,住在陆浑山中。山中有个老虎经常出来祸害人。尹轨让黄理把树锯成柱子,离他家五里的地方,在东西南北四方各埋一根木柱,埋好后,尹度在柱子上打上封印,此地老虎便绝迹了。老虎如果来也是走到五里地埋柱子的地方就不敢再往前走。有一家屋上停着一只怪鸟,这家人来找尹轨,尹轨就写了一道符,让哪家人把符贴在怪鸟叫的地方。到了晚上哪怪鸟死在了符下。有一家死了人,由于太穷没法办理丧事。尹轨前去这家看望,孝子向他哭诉家中的困境,尹轨心里很难过,就让孝子找了一小块铅来。尹轨带着铅进了荆山,在山中搭了个小屋,在小屋中生起炉火把铅熔化,然后把自己所带的药弄了米粒大的一点投进铅水里,搅了一阵,铅就变成了好银子。尹轨把银子送给那孝子,并对他说:“我可怜你家里太穷不能治丧,所以帮你一把。你千万不要对别人说我用铅炼银的事!”有个人欠了官府百万钱,官府要捉住他,尹轨就从富人那里借了几千钱给那人,让他买来一百两锡。尹轨把这一百两锡用火熔化了,然后留了一方寸那么大的一匙药投进去,锡就变成了一百两黄金,让他还给了官府。后来尹轨进了太和山(今在山西朔县)成仙而去。
涂抹药物法是将药物涂抹在身体表面组织或某一部位,以达到消毒防疫的作用,涂抹部位一般为额上、五心、鼻人中及耳门等处。《肘后备急方》指出涂抹药物法可用于预防瘟疫,曰:“姚大夫《辟温病粉身方》⑧……以涂粉于身,大良;赵泉黄膏方……以摩身体数百遍;佳;赤散方……亦宜少许以内粉粉身佳。”《备急千金要方》亦记载涂抹药物法的一些要方:“辟温气,雄黄散方……以涂五心额上鼻人中及耳门;辟温病,粉身散……以粉身。”
注释⑧:《辟温病粉身方》伤寒、温病用药大体及辟温方:凡除热解毒,无过苦醋之物,故多用苦参、青葙、艾、葶苈、苦酒、乌梅之属,此其要也。夫热盛非苦醋之物则不能愈。热在身中,既不时治,治之又不用苦酢之药,如救火不以水,必不可得脱免也。
又曰∶今诸治多用辛甜、姜、桂、人参之属,此皆贵价难得常有,比行求之,转以失时。
而苦参、青葙、葶苈子、艾之属,所在尽有,除热解毒最良,胜于向贵价药也。前后数参并用之,得病内热者,不必按常药次也。便以青葙、苦参、艾、苦酒治之,但稍与促其间耳,无不解。(《外台》卷三)
断温方:二月旦取东行桑根,大如指,悬门户上。又人人带之。(《医心方》卷十四)。
断温病,令不相染着法。
断汲水绠,长七寸,盗着病患卧席下。(《医心方》卷十四)
辟温病粉身方:川芎、苍术、白芷、零陵香各等分,三物等分,下筛,内粉中,以涂粉于身,大良。(《肘后方》卷八)
疾疫流行预备之,名为柏枝散方∶南向社中柏,东向枝,取曝干,末,服方寸匕,神验(《肘后方》卷八)。
(二)管理卫生法
(1)环境卫生
在阻断瘟疫传播的过程中,搞好环境卫生作用重大,包括空气和水源环境等。消毒法是搞好空气卫生的主要方法。《肘后备急方》和《备急千金要方》均提出诸多用于辟瘟疫的空气消毒法,如太乙流金方、虎头杀鬼方等,通过烧熏法、佩挂法或涂抹法进行大面积或局部空气的消毒,该法尤其以经空气传播传染病的预防效果佳。
水源卫生是人体健康的重要保障,也是瘟疫时期整治的重要对象。《备急千金要方》记载“岁旦屠苏酒方⑨”用于井水消毒,可预防瘟疫,曰:“岁旦屠苏酒方:饮药酒得三朝,还滓置井中……当家内外有井,皆悉着药,辟温气也。”此外,《肘后备急方》记载的辟温疫的单行方术:“又各二七枚投井中,又以附子二枚,小豆七枚,令女子投井中。”以及《急备千金要方》记载的断瘟疫方:“正旦吞麻子、赤小豆各二七枚,又以二七枚投井中。”均提及对井水投以小豆等药物,可起到杀虫消毒的作用。水源消毒法尤其以经水传播传染病的预防效果较佳。
注释⑨:《岁旦屠苏酒方》------预防瘟疫毒菌:大黄、桔梗、署椒各十五株,白术、桂心各十八株,乌头六株,菝葜十二株。一方有防风一两。
上七味咀,绛袋盛,以十二月晦日日中悬沉井中,令至泥,正月朔日平晓出药,置酒中煎数沸。
辟疫气,令人不染温病及伤寒。
於东向户中饮之,屠苏之饮,先从小起,多少自在。
(《备急千金要方》)
(2)个人卫生
在阻断瘟疫传播的过程中,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不容忽视,包括沐浴习俗和饮食习惯等。
道教注重药浴习惯,用于预防疫病。药浴法是将药物作为沐浴汤,通过药浴来辟疫。据《备急千金要方》记载:“凡时行疫疠,常以月望日,细剉东引桃枝,煮汤浴之。”当瘟疫横行时期,煮药汤沐浴,可防疫。书中还指出,针对新生儿可采用“浴儿法”进行避疫,使其终身不患疮疥:“儿生三日,宜用桃树根汤浴……浴儿良,去不详,令儿终身无疮疥。”
不良的饮食习惯是导致疾病产生与流行的因素之一,道教对此已有认识并列举预防瘟疫的饮食禁忌。葛洪指出:“凡所以得霍乱者,多起饮食,或饮食生冷杂物。”孙思邈亦表示:“夫霍乱之为病,皆因饮食,非关鬼神。”可见,二人均将霍乱的起因归结于饮食因素,认为饮食生冷或不洁导致疾病发生。故葛洪明确告诫禁止食用自死性畜生,否则将导致疾病。曰:“六畜自死,皆是遭疫,有毒,食之洞下,亦致坚积……几物肝脏,自不可轻啖,自死者,弥勿食之。”孙思邈提出“不知食宜者,不足以存也”,告诫“勿食生肉,伤胃,一切肉惟煮烂”。以避免病从口入。并引用“黄帝云:七月勿食生菱芰,作蛲虫”,指出不可生食菱芰,否则招致蛲虫病。
(三)保护易感人群
易感人群是指对传染病病原体缺乏免疫力,易受感染的人群。现代医学保护易感人群措施主要有免疫预防、药物预防和个人防护等,道教保护易感人群措施多属养生术。葛洪注重防治于先的养生思想,《抱朴子》记载:
或问曰:“为道者可以不病乎?”抱朴子曰:“养生之尽理者,既将服神药,又行气不懈,朝夕导引,以宣动荣卫,使无辍阂,加之以房中之术,节量饮食,不犯风湿,不患所不能,如此可以不病……又多令人以针治病。”
道教认为养生术可预防疾病,具体包括饮食法、服药法、行气法和导引法等。此外,还有针灸法。另外,免疫接种法作为现代防疫的重要措施之一,在古代也同样受到道教的推广。
1.饮食法
道教医书少有记载预防瘟疫的食物种类,多强调饮食对于身体健康的重要性,通过正确的饮食可增强易感人群的抗病能力。
《黄帝内经》反复强调饮食对脾胃的重要性,认为“人以水谷为本”,四季皆“以胃气为本”,“胃不和则精气竭”。若饮食不节,饥饱无常,不但损伤脾胃,也会影响五脏和精气,降低抗病能力。《太平经》认为控制饮食可去除百病,曰:“食无形之物看,节少为善……节食千日之后,大小肠皆满,终无料也,令人病悉除去,颜色更好,无所禁防。”
葛洪提倡以豉术酒辟疫,曰:“豉杂土酒渍,常将、服之……熬豉新米酒渍,常服之。”孙思邈亦用此豉术酒方“治温令不相染”,并强调饮食的重要,曰:“安身之本,必资于食;不知食宜者,不足以存生。”并提倡饮食宜有规律,不可吃得过饱,要常处于一种半饥状态。曰:“先饥而食,先渴而饮,食欲数而少,不欲顿而多,则难消也。常欲令如饱中饥、饥中饱耳。”
2.服药法
服用方药是道教预防瘟疫的重要举措。
《素问·遗篇》较早提出服用“小金丹方”预防疫病,曰:“小金丹方:辰砂二两,水磨雄黄一两,叶子雄黄一两,紫金半两……服十粒,无瘟疫传染也。”《肘后备急方》对于伤寒时气温病的预防,指出:“又方:大黄三两,甘草二两,麻黄二两,杏仁三十枚,芒硝五合,黄芩一两,巴豆二十粒熬,捣,蜜丸和如大豆,服三丸,当利毒。利不止,米饮止之。家人视病者,可先服取利,则不相染易也。”即探望病人的家属,事先服用该丸泄下,就能避免被传染。此外,还记载了避瘟疫的诸多内服药方,如辟瘟疫药干散、老君神明白散、赤散方、度瘴散、辟天行疫疠、常用辟温病散方、赵泉黄膏方和单行方术等。以及断温病的诸多又方,如常服小豆、熬豉、酒渍等可断温病,令不相染。
孙思邈云:“天地有斯瘴疠,还以天地所生之物以防备之。”认为疫病可通过服用药物预防。他在《备急千金要方》中列举了诸多辟温方,收录并补充了《肘后备急方》的部分防疫方剂,如岁旦屠苏酒方、柏枝散方、辟温杀鬼丸、雄黄丸方和赤散方等。还主张以“金牙散”防治南方瘴疠等疫病,指出常服吞麻子、赤小豆、酒渍等可断温病,令不相染。
3.行气法
行气法,是通过壮大身体之气,提高人体免疫力,从而达到无病的目的。
《摄养枕中方》收入《云笈七签》卷三十三。强调行气功效诸多:“行气可以治百病,可以去瘟疫,可以禁蛇兽,可以止疮血,可以居水中,可以辟饥渴,可以延年命。”葛洪也指出行气的诸多功效,如“行气可以不饥不病”;又如“行气或可以治百病,或可以入瘟疫,或可以禁蛇虎,或可以止疮血,或可以居水中,或可以行水上,或可以辟饥渴,或可以延年命”。其所谓“行炁”,同“行气”,具体内容为“春向东食岁星青气,使入肝;夏服荧惑赤气,使入心;四季之月食镇星黄气,使入脾;秋食太白白气,使入肺;冬服辰星黑气,使入肾”。
行气法:有时也配以存思法,即在行气时通过精神层面的自我暗示,使得精神内守、真气和顺,从而预防疾病的发生。《素问》指出运用意念引导正气运行的方法,可以使未患病之人进入疫病病室而不被感染,曰:“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避其毒气……气出于脑,即不干邪……然后可入于疫室。”即运用意念依次想象心中作上述想象,则有了五脏之气及自然阳气保护身体,即可进入疫室。这种五气护体法自以为可达到正气护身、邪气难侵的目的,蕴含着心理暗示作用。
4.导引法
导引法以肢体运动为主,是配合呼吸吐纳的养生方式,以强身防病。
《诸病源候论》收录有关防治疫病的导引法,如“温病候,养生方导引法云,常以鸡鸣时,存心念四海神各三遍,辟百邪止鬼,令人不病”。又如“延年之道,存念心气赤,肝气青,肺气白,脾气黄,肾气黑,出周其身,又兼辟邪鬼。欲辟邪却众邪百鬼,常存心为炎火如斗,煌煌光明,则百邪不敢干之,可以入温疫之中”。均强调导引法具有辟邪驱鬼、预防疫病的功能。
葛洪认为疾病要防治于先,指出导引法作为祛除疾病的玄术,可防治疾病发生,故曰:“导引疗未患之疾,通不和之气,动之则百关气畅,闭之则三宫血凝。实养生之大律,祛病之玄术矣。”强调应在年少与壮时就应该开始注意养生,曰:“恃年纪之少壮,体力之方刚者,自役过差,百病兼结,命危朝露,不得大药,但服草木,可以差于常人,不能延其大限也。”孙思邈亦云:“养生之道常欲小劳,但莫大劳及强所不能堪尔。”提倡养生应劳逸结合,提倡根据体质、年龄的差异选择合适的导引方式。
5.针灸法
针灸是中国传统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道教防治瘟疫的重要手段。
采用针灸法预防疫病首见于《黄帝内经》,《灵枢·逆顺》曰:“上工,刺其未生者也;其次,刺其未盛者也;其次,刺其已衰者也。”针灸法不仅可用于治疗发病的患者,还可以用于未患病者,保护易感人群,避免疾病发生。《灵枢·刺法论》曰:“可以折郁扶运,补弱全真,泄盛蠲余,令除斯苦……以法刺之,预可平。”针刺五脏,可疏通经脉,预防温疫。
灸法是一种温热刺激疗法,具有增强机体抵御外邪的能力。孙思邈提出用灸法预防疟疾等传染病,曰:“凡人吴蜀地游宦,体上常须三两处灸之,勿令疮暂瘥,则瘴疠温疟毒气不能著人也,故吴蜀多行灸法。”他还提倡无论是在家中还是出门远行,最好随身携带熟艾一升以便行灸法,用来预防疫病。
6.免疫接种法
免疫接种是用人工方法将免疫原或免疫效应物质输入到机体内,使机体通过人工主动免疫或人工被动免疫的方法获得防治某种传染病的能力。
早在东晋时期,葛洪就发明了狂犬病的人工主动免疫法:“疗吠犬咬人方,乃杀所咬犬,取脑傅之,后不复发。”利用狂犬脑髓干粉敷在伤口处治疗狂犬病,这被认为是人类对于免疫接种的最初探索,其思想与后来的巴斯德预防狂犬病原则一致。此外,据《备急千金要方》记载:“治小儿疣目方:以针及小刀子决目四面,令似血出,取患疮人疮中汁黄脓傅之,莫近水三日,即脓溃根动,自脱落。”唐代孙思邈曾尝试以“以毒攻毒”的思想,用脓汁、血清接种的方法防治小儿疣目症。马伯英在《中国医学文化史》中将孙思邈的防治小儿疣目症的方法称为“种疹法”,并指出预防的思想和方法在唐代就已存在,曰:“《千金要方》有‘种疹法’,……总之,预防思想和方法在唐代已有生发。”
“以毒攻毒”的思想已近乎近代免疫学思想,在该思想的指导下,逐渐产生用于防治天花的中国种痘术——“人痘术”。《痘疹定论》称种痘术乃源于宋真宗时峨眉山顶的种痘女神医“天姥娘娘”,书中详述该女神医为丞相王旦之子王素种痘及传播种痘术的事迹。《广布天花说及符法》记载了整个种痘过程中必须进行的道教祈禳仪式及众多相应的用符诸法,透露种痘术盖乃初传道教仙传。《种痘指掌·种痘原说》亦透露种痘术乃传自道教真人,可以窥见道教在免疫接种方面的贡献。
历史上每次大的瘟疫流行都会夺去无数人的生命,致使妻离子家破人亡,出现“万户萧条鬼唱歌”的悲惨状况。由于瘟疫的传染性,未经妥善安置的尸体将进一步传染疾病,危害家人和环境。西汉时期,平帝曾下诏,按每家死于瘟疫的人数赐与不等的安葬费。唐朝时期对瘟疫时期掩埋尸体十分重视,唐太宗曾派使者沿城巡行,发现尸骸迅速掩埋。唐玄宗在大疫其间下令,死者尸体一定要家人掩埋,无人管者,由地方官负责安置。唐文宗时规定,患瘟疫家庭留下来的遗孤,如不满是十二岁,一定要由亲属负责养育,官府提供两个月的口粮救济,孤儿名单要上报官府。这些措施和作法,不但是施行人道,保护生命,还起到了安定民心和社会的作用。
如上所述,中国古代是采用多种多样的方法来综合治理瘟疫的。千百年来的抗疫实践证明这些古老的方法行之有效,即使在科学技术和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预防现代瘟疫使用的方法仍然大同小异。应该看到,近百年来,随着社会文明和科学发展的不断进步,人类对付瘟疫的办法愈来愈多,手段也逐渐提高,其结果是传染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大幅度下降,人类的生活质量和寿命明显升高。现在人类可以骄傲的说在同病魔的斗争中人类已经真正做到了“道高一丈”。但是,切切不要忘记,瘟疫向人类的进攻从来没有停止过,瘟疫不时还会司机发动反击,而不时出现“魔高一尺”的情景。人类注定要病魔长期共存。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转载请注明:http://www.ohhayoungchina.com/hthl/1567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