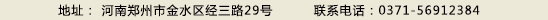徽商儒商与官商
白癜风学术交流峰会 http://m.39.net/pf/a_6210224.html明万历年间有书记载:“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新安大贾,鱼盐为业,藏镪有至百万者,其他二三十万,则中贾耳。”新安即徽州,山右即山西。意思是说,最富有的当属南方的徽商和北方的晋商。清朝国力最为强盛之时是乾隆时代,当时国库存银高达多万两,以国为家的乾隆皇帝却感叹说:“富哉商乎,朕不及也!”他所说的“商”就是徽商。与山陕商人类似,明清两代,徽商主要依靠茶和盐的垄断性经营,积累了大量财富,成为中国最著名的传统商帮。徽商,指的是出自徽州的商人集团。徽州地处“吴头楚尾”,这里山高林密,人口稀少,发展一直较为滞后。晋末、唐末和宋末,北方游牧民族入侵和中原战乱,先后引发了三次大规模的移民潮。北方难民为躲避战乱而大量迁入徽州,这里才开始繁荣起来。据说徽州的名称来自宋徽宗。中国古代有四民之分,农本商末,但这种观念主要是基于统治,而非为了人民生计。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序》里说:“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也就是说,一个社会必须有四个基本行业:有农业,才有饭吃;有虞业(采集业,包括打猎、伐木、捕鱼、采矿等),才能够把重要自然资源开发出来;有工业,才能把各种原料加工成为用具;有商业,才能够把各种货物流通天下。明代王阳明同样主张四民并列:“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士以修治,农以具养,工以利器,商以通货。”常言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徽州人经商,也离不开其天然的地理优势。他们最早是向外贩运石材和木材,尤其是南宋初期,首都迁到杭州,城市营建,需要大量的建材;徽州人占有地利之便,从徽州沿新安江下行,就进入浙东富春江,再往下就是钱塘江,最后到达杭州。虽然有崇山峻岭,但水路极其便捷,一路顺风顺水,运输成本很低。徽州地形多山,“其地险狭而不夷,其土驿刚而不化”,适合耕种的土地极少,所谓“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为了多一些土地,人们不得不在山上开垦梯田;但山势陡峭,即使十数级梯田,加起来也不够一亩。这种石头缝里求生存的农耕,说起来条件非常艰辛,远非平原地区的人们所能想象的。穷则思变,徽州人不得不另寻出路,吴日法在《徽商便览》中说:“吾徽居万山环绕中,川谷崎岖,峰峦掩映,山多而地少。遇山川平衍处,人民即聚居之。以人口孳乳故,徽地所产之食料,不足供徽地所居之人口,于是经商之事业起。”“人人皆欲有生,人人不可无贾矣。”人地矛盾的压力之下,经商逐渐取代农业,成为徽州人的“第一等生业”。据说在徽州成人男子中,有超过七成的人以经商为生。徽商因此而闻名天下。“丈夫志四方,不辞万里游。”按照徽州当地的风俗,一般男孩子从十几岁就要跟着长辈外出,从伙计开始,学着做生意。如果学徒期未满就回家,或者生意蚀本,空手而归,都会被家乡人看不起。所以,从一开始,徽州人就有一种破釜沉舟的意志,他们背井离乡,别妻离子,一年到头四处奔波,为了生意,兢兢业业,不遗余力,不成功便成仁。徽州人“诡而海岛,罕而沙漠,足迹几半宇内”,胡适先生因此把徽商称为“徽骆驼”。对经商的追求,徽商比之于晋商和陕商,有过之而无不及。有时候他们数年才能回家小住一次,大多数人都要等到年老体衰,才回家养老,真是少小离家老大回,黑发出门白发归。一首《新安竹枝词》写道——健妇持家身作客,黑头直到白头回。儿孙长大不相识,反问老翁何处来。无徽不当在传统的中国社会,商人属于“四民”之末。但徽州人从思想观念上颠覆了这一偏见,宣扬“士、农、工、商皆为本业”“士商异术而同志”“四民异业而同道”。在徽州人看来,“读书贵矣,但农、工、商、贾各专一业,便非不肖子孙”。保留至今的徽州黟县西递村已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名录”,这里有一副著名的楹联:读书好,营商好,效好便好;创业难,守成难,知难不难。徽商经营的商品,以“盐、典、茶、木为最著”。徽州有丰富的茶叶和木(竹)材资源。特别是明清时期,茶叶不仅是中国人的必需品,后来还发展成为中国出口到全世界的重要商品,徽州商人因此迅速壮大,商业网络甚至延伸到国外。与茶叶类似,盐也是徽商得以纵横天下的核心商品,和晋商陕商一样,徽商因茶盐而起。明朝初年,以“开中法”解决军需,“召商输粮而与之盐”,一批徽州商人成为盐商。弘治时期,开中制改折色制,两淮和江浙地区成为盐业贸易的中心,徽商近水楼台先得月,逐渐取代山陕商人,执中国盐业之牛耳。因为盐业属于明清两代政府的财政支柱,实行官督商销的垄断政策,徽州商人依靠官商身份,获得了高额垄断利润,积累了大量财富。明朝时期就不乏百万级的富商,歙县盐商“以盐筴祭酒(总商)而甲天下者,初则黄氏,后则汪氏、吴氏,相递而起,皆由数十万以汰百万者”。值得一提的,嘉靖年间著名的倭寇首领汪直原本也是一位徽州盐商,后来成为从事海外贸易的大海商。海禁时期,他以日本为据点,从事武装走私。当时很多走私海商(海盗)都将头剃成日本武士的发型,变身为对抗明廷的“倭寇”。汪直自称“徽王”,几乎控制了东南亚与中国、日本之间的交易。汪直吸引来中国和葡萄牙的商人,使平户成为一个繁荣的贸易港。嘉靖三十八年(年),汪直死在杭州,而此前招安他的是另一个徽州人——浙江福建都御史胡宗宪。入清之后,徽州盐商的资本更是发展到了千万级别。徽商汪福光手下仅运盐船就上千艘,所销之盐占淮盐之半。徽商与扬州密不可分,与其说扬州因盐而兴,不如说是因徽商而兴。从明代中期到清代乾嘉年间,两淮盐商均以徽商为主体。据《扬州画舫录》记载,扬州的著名徽商有马、鲍、郑、巴、江、黄、吴、徐、程九个家族,共八十一人。徽商称雄扬州,不仅人数众多,更重要的是他们资本雄厚。扬州从事盐业的徽商,掌握着超过四千万两银子的资本,真正是富可敌国。陈去病《五石脂》中这样说:“扬州之盛实徽商开之,扬盖徽商殖民地也。”典当业作为古代中国的民间银行机构,在传统商业占有重要的地位。明清两代,徽商在典当业实力非凡,乃至有“无徽不当”之说。不像其他大宗商品交易,经营当铺需要大量的专业知识,徽州休宁人便长于此道——“治典者亦惟休(宁)称能。凡典肆无不有休(宁)人者,以专业易精也。”除了茶、盐、木、典,徽州商人在粮食、棉布、丝绸、土漆等方面也极其活跃,特别是笔墨纸砚——即歙砚、徽墨、澄心堂纸、汪伯立笔等俗称“文房四宝”,徽州人几乎拥有垄断性的地位。在餐饮、旅店、药材、杂货、出版、渔业等方面,也不乏徽商的身影。分家不分店清代有一部笔记小说中,讲述了两个徽州商人靠一文钱起家的故事。两位安徽商人到苏州经商,遇到灾祸,沦落为乞丐。晚上二人栖身在破旧的古庙中,甲唉声叹气,感叹如今一文不名;乙从身上摸出一文钱,说还有一文钱呢。二人破涕为笑,想来想去,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他们用这一文钱买了一些面粉,调成浆糊,然后用捡来的鸡鸭羽毛、破纸竹片,做了许多玩具,在集市上卖给妇人小孩,结果赚了几千文。他们就这样做了两年玩具生意,竟也积攒起一笔不小的资产,便在苏州城开了一家大商铺,名字就叫“一文钱”。实际上,无论做哪种生意,都需要大量的资本,盐和茶更是如此。在清代两淮盐场,经销一纲盐,往往需要两千多万两本银。如果经营茶叶,就要在茶叶采摘之前先付茶农定金,缴付税款,再加上茶叶的采摘、加工、包装和长途运输,没有巨额资金根本不行。徽商的这些本金,一般都是来自宗族范围内的借贷。因为借贷发生在同乡同族内部,所以一般利息较低,甚至无息,这使得徽商能够以较低的资金成本,获取最大的商业利润,从而发家致富。作为传统商帮,徽商与陕商、晋商一样,都有浓厚的宗族文化色彩。山陕商人建设了大量的山陕会馆,供奉着关公;徽商也修建了许多会馆,供奉的是朱熹。徽商完全依据血缘和地缘关系,形成了一个非常牢固和信任的商业共同体,在组织内部休戚与共,齐心合力,形成极强的竞争力,“挈其亲戚知交而与共事,以故一家得业,不独一家食焉而已。其大者能活千家百家,下亦至数十家数家,且其人亦皆终岁客居于外,而家居者亦无几焉”。很多经济史学家在谈起古代中国未能出现资本主义时,常常将矛头指向中国的分家传统。西方观念中,一般由长子继承家产,中国则由多子平分,这导致财富分散化,难以形成大的资本。徽商则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他们在许多不同的行业中,常常以合资经营的方式,保证了资本的完整性。如歙县盐商鲍志桐与家居仰山的堂兄合资经营,十年时间积累上万资产。徽州人通常是“分家不分店”,非商业性的一般田产和房屋可以分,但店铺与公田不能分,这一方面避免了资本的分散,另一方面也加强了宗族的凝聚力。每个人名下的资本以股份形式投入经营,资本拥有者以投资者身份获得相应股份和分红,这是一种良性循环。值得一提的是,家族中人还可将自己的闲散资金作为“附本”投入,在获得商业回报的同时,也扩大了经营资金的来源。无徽不成镇徽州人大多都是南迁的中原士族后代,在长期的战乱和迁移中,宗族文化得到了极度的强化,再加上程朱理学的影响,徽商非常注重宗族传统和儒家文化。这是农民色彩强烈的山陕商人无以比拟的。徽州人一般聚族而居,经商也是一种全族行为,因此商业组织往往是家族性的,举族上下成百上千人,根据每个人的性格特长,构成一个牢固严密的商业团体。对徽商来说,他们不仅修建会馆,更喜欢修建宗族祠堂,将族谱和祭祖看得特别重。歙县汪氏家族《汪氏谱乘》开篇写道:吾汪氏支派,散衍天下,其由歙侨于扬,业卤两淮者则尤甚焉。居扬族人,不能岁返故里,以修禴祀之典,于是建有公祠。凡值春露秋霜之候,令族姓陈俎豆、荐时食,而又每岁分派族人专司其事。数十年来,人物既盛,而礼文器具未尝稍弛。徽商一生漂泊,就是为了一朝发迹,衣锦还乡,光宗耀祖。对徽商来说,宗族是其生存的根本,不仅资金和人才来自宗族,而且其管理和文化也完全来自宗法传统。可以说,没有强大的宗族文化,就不可能有徽商。不同于陕商和晋商,徽商更注重儒家教育,贾而好儒,“贾者力生,儒者力学”。经商是为了生存,尊儒才能上进,所谓“贾为厚利,儒为名高”。与北方的山陕相比,徽州的教育水平在明清时期达到相当高的程度,“十户之村,不废诵读”。家族重视,商人资助,延请名师,建设各种学堂试馆,从而徽商中人才辈出,有“连科三殿撰,十里四翰林”之说。明清时,徽州五县就出了个进士。中国现代史上赫赫有名的胡适先生就出身徽商家庭。古代中国是“学而优则仕”,“官(士)”为四民之首,“商”为四民之末,有这些徽州子弟担任高官,徽商自然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政治话语权,他们的商业利益也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保护。如出身徽商世家的徐承宣官工科掌印给事中时,“扬州五塘关政滋弊,承宣谓此关外之关,税外之税也。慷慨力陈,一方赖之”。与喜欢买虚职官衔的山陕商人相比,徽商对“官”与“商”的结合更加紧密,他们的行为作风,基本摆脱了底层农民的色彩,体现出精英化的士大夫情结;用戴震的话说,就是“虽为贾者,咸近士风”。就徽商而言,儒教伦理与商业主义精神结合得非常紧密。由仕而商,多少也是有些迫不得已。从明到清,中国人口增加了几倍,但入仕名额并未增加,科举竞争极其激烈,中举者不到1%,大批落榜秀才只能走上经商之路。经商需要记账立约,读书人从商比较容易。《丰南志》记载,明末就有“士而成功也十之一,贾而成功也十之九”之说。歙县《竦塘黄氏统宗谱》中记载,黄崇德弃儒从商,到山东贩盐,最后成为大商人。徽商与他们的祖先一样,以经商的方式继续着移民生活;他们随着生意的发展而散落各地,但仍保留着宗族这个牢固的纽带。徽州人走到哪里,哪里就会因商业而繁荣起来,因此便有了“无徽不成镇”之说。胡适先生对徽州人有一段评论——徽州人正如英伦三岛上的苏格兰人一样,四出经商,足迹遍于全国。最初都以小本经营起家,而逐渐发财致富,以至于在全国各地落户定居。因此你如在各地旅行,你总可发现许多人的原籍都是徽州的。例如姓汪的和姓程的,几乎是清一色的徽州人。其他如叶、潘、胡、俞、余、姚诸姓,也大半是源出徽州。金钱与堕落尊儒传统使得徽商与陕商、晋商极其不同,徽商作为民间商帮体现出深厚的文化底蕴。明清时期,官僚阶层都是读书人出身,商人要在官僚统治下生存,有读书人身份无疑要优越得多。徽商传统上重视教育,教导子弟熟读经书,不是进入仕途为官,便是下海为儒商。因为这种“师出同门”的机缘,徽商与官僚的关系更加密切,如鱼得水,相得益彰;共同文化语境下的官商一体,一方面使徽商能够依靠权力的庇荫而一支独大,另一方面也导致徽商后来随着传统权力的瓦解而走向没落。有清一代,徽商几乎垄断了两淮地区的盐业,扬州盐商大多出自徽州。康熙和乾隆多次驾临扬州,徽商每次极尽逢迎。可以说,康熙皇帝六次南巡、乾隆皇帝七次南巡,这些费用也都由徽商所出。有人推算,扬州盐商手中积累的商业资本基本与清朝国库不相上下。因为盐业专卖制度,徽商与官府自然结成利益共同体。为了使这种关系更加可靠,徽商非常鼓励天资聪颖的子弟走读书科举之路,这已经不像早期那样,让孩子优先学做生意。小生意固然可以不需要官府背景,但大生意如果没有官府支持,根本难以为继。对资产丰厚的徽商来说,最保险的办法莫过于让自己的子弟当官做后盾。据嘉庆《两淮盐法志》记载,从明洪武后期至清嘉庆前期,两淮共有陕西、山西、徽州籍科举职官人,其中陕西96人、山西21人,而徽州多达人,占71%,远超山陕商人。清中后期的政局中,出身徽商的官吏群体已经崭露头角。如出身盐商的曹文埴、曹振镛父子,二人都曾担任军机大臣,并历经乾隆、嘉庆、道光三朝。根据何炳棣先生在《明清社会史论》中的统计分析,明代科举中,平民出身的进士约占总数的50%,清代则减至37.2%;而出身官宦之家者,则由明代的50%,升至清代的62.8%;可见平民向上流动的机会已经减少。清代,尤其清代后期,大行捐纳制度,富与贵紧密结合,有钱才能做官,做官才能有钱。朝中有人好做官,朝中有人更好经商。官府与徽商之间存在一种默契,这些徽商子弟不仅被准许在行商省份附籍入试,还享有另立学额的优遇权;这样一来,其子弟的中举率要远远高出常人许多。如果家族中没有当官的,就只能用各种方法巴结官员。为此,徽商不惜慷慨解囊,为朝廷捐输报效,用大把的金银对盐政衙门和盐官“效忠”。徽商鲍志道是乾隆年间的两淮总盐商,他先后向清政府捐赠白银万两,粮12万余石。清朝盐业实行官督商办,就是国家只出售限量的许可证,而不直接买卖食盐。在完全的垄断体制下,乾隆时代食盐的购价与销价相差三四倍。徽商与官府的畸形关系,催生了扬州奢靡的消费文化。徽商“侈靡奢华,视金钱如粪土,服用之僭,池台之精,不可胜纪”,“衣服屋宇,穷极华靡,饮食器皿,备求工巧;俳优伎乐,恒舞酣歌;宴会戏游,殆无虚日,金银珠贝,视为泥沙;……骄奢淫佚,相习成风。各处盐商皆然,而淮扬尤甚”。为了讨好官吏和皇帝,徽商热衷于修建园林、豢养文人和妓女,也使徽班和徽菜盛极一时。与《清明上河图》齐名的《扬州画舫录》出自清代画家李斗之手,它逼真地描绘了扬州徽商的奢侈生活。用经济史学家何炳棣先生的话说,徽商生活腐化是其自身的需要,不只是为了享受和炫耀,因为他们要以此来结交和贿赂官员。徽商的没落亦官亦商,亦儒亦商,这并不是说徽商的生意毫无风险、稳赚不赔。在中国传统观念中,商人是“富而不贵”,虽然有钱,但却没权,因此社会地位不高,他们既是官府的小肥羊,也是官府的替罪羊。权力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随着清后期财政越来越吃紧,徽商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乾隆时,盐税每引只有12两,之后就徽商需要缴纳的税费越来越多。羊毛出在羊身上,超高的负担最后必然会转嫁给食盐者。盐价高涨,以至于吃盐花费占到普通人收入的三成到四成。官盐吃不起,私盐日渐泛滥,徽商处境日益艰难。道光十一年(年),两江总督陶澍为革除淮盐积弊,对盐业专卖制度实行改革,改行票法,运销分离之后,剥夺了徽商对盐业的垄断特权,这对徽商构成致命打击。徽州盐商受惠于官府的庇护,凭借其垄断地位才获得高额利润,从而积累了大量财富。据乾隆年间的统计,两淮产盐在当地每斤值钱十文,加上税银七文,每斤成本值钱十七文;而运销到湖北等地,每斤可以卖到五六十文不等。盐商向来是徽商的中坚力量,就因为官府的不支持,一下子失去举足轻重的传统地位,沦为普通盐商,真所谓“成也官,败也官”。江春的遭遇堪称徽商盛极而衰的一个缩影。江春长期担任两淮盐业总商,袁枚称之为“以布衣上交天子”“身系两淮盛衰者垂五十年”。江春一方面通过盐业特权获得了巨额财富,另一方面又因为报效捐输和无度挥霍而千金散尽,最后竟陷入了“贫无私蓄”的困境。乾隆五十四年(年),曾经富可敌国、官至一品的江春贫病而死,身后没有留下什么家产,其子江振鸿几乎沦为乞丐。实际上,晚清著名“红顶商人”胡雪岩比江春更能代表徽商的命运。胡雪岩年轻时在钱庄做伙计,资助王有龄赴京补缺,王后来官至浙江巡抚,胡雪岩因此发迹。王死后,胡雪岩投靠左宗棠,协助其办洋务,创建福建船政局,订购西洋军火。胡以此为资本,从事贸易,在各市镇设立商号,广泛涉及典当、丝、茶、药诸业,利润丰厚,短短几年,家产超过千万。晚清时期的大官僚和军阀身边,都少不了这类“红顶商人”为其运作资金:李鸿章用盛宣怀;左宗棠用胡雪岩;张之洞卸任山西巡抚后,公私业务仍由平遥“百川通”票号打理。胡雪岩主要依靠左宗棠的权势,帮助清政府借款、买办等特殊的政商生意,并借助这些高官和军队的公私存款,进行包括钱庄、当铺、药局和生丝进出口等生意。当时胡雪岩名声之大,几乎天下皆知。《异辞录》记载,胡雪岩“藉官款周转,开设钱庄,其子店遍布于南北,富名震乎内外。官商寄顿钱财,动辄巨万,尤足壮其声势”。“雪岩”二字本为“冰山”之意。胡雪岩最得意时官居二品,赏穿黄马褂,被称为“活财神”“江南药王”。转眼失势,便成为千古罪人,“亏欠公项及各处存款为数甚巨”,落得家产尽没,郁郁而终。晚清时期,天灾人祸频发,太平天国战争引发长时间的兵燹劫难,这对徽商的打击更加沉重和致命。曾国藩曾描述到:“自池州以下,两岸难民,皆避居江心洲渚之上……老幼相携,草根掘尽,则食其所亲之肉。……徽、池、宁国等属,黄茅白骨,或竟日不逢一人。”徽商云集的扬州明末时曾被满清八旗屠城,晚清时再遭厄运。南京是徽州木商的集中地,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禁商”,“天下农民米谷,商贾资本,皆天父所有,全应解归圣库”。清军与太平军在皖南展开拉锯战,十村九毁,十室九空。战争过后,在洋商和洋货的冲击下,徽州茶叶、生丝和棉布贸易也一落千丈。同时,清政府对典当业进一步提高税率并预征典税,再加上现代银行业的兴起,颇受徽商倚重的典当和钱庄也遭受重创。在帝国的余晖下,曾辉煌几个世纪的徽商无可挽回地走向衰落。英国与中国在茶叶贸易上存在巨大的逆差,英国试图以鸦片贸易来平衡贸易逆差,结果引发了鸦片战争。战争之后,印度茶叶逐渐取代了中国茶叶在国际市场上的垄断地位,徽州茶商一蹶不振;再加上落后的加工技术和高额的厘金,这场灾难完全是灭顶式的打击,不仅茶商破产,连带徽州的茶农也深陷困境。一些史料记载:“今日东洋产绿茶,印度产红茶,均免出口税,则又用机器制造,成本甚廉,行销甚广。故中国之茶日形壅滞,无不互相贬价,年甚一年,近来各商罢业居多,综合出口茶叶,较之从前销数十绌其四五矣。”当时的皖南茶厘总局的资料记载,光绪十一年(年)至十三年(年),亏本自三四成至五六成不等,已难支持;十三年亏折尤甚,统计开银将近百万两,不独商贩受累,即皖南山户园户亦因之交困。在整个徽州地区,“以业茶破家者十有八九”。作为传统商人,徽商所经营的商品属于传统的手工业制品;随着晚清现代大变局,价廉物美的西方工业产品大量进入,如文房四宝被钢笔墨水取代,传统手织棉布被机织布取代。更残酷的是传统商业知识被时代淘汰,一些传统行业直接被新兴产业颠覆,如银行取代了钱庄。在这场天翻地覆的历史大变局中,比徽商更有地缘优势的广东和江浙商人,与西方殖民势力和军阀官僚结为新联盟,在商业和经济领域占据了优势地位,徽商被完全边缘化。应当承认,徽商之所以在清朝末期衰落,更深一层的原因是传统儒家文化的衰落。在全球化的现代浪潮涤荡之下,中国传统社会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变革和震荡。徽商所依重的茶丝国际贸易江河日下,盐业经营也陷于崩溃。事实上,徽商与陕商、晋商殊途同归。传统商帮的没落,只不过是大清帝国走向末日的一个缩影而已。徽商的遗产顾炎武说:“新都勤俭甲天下,故富亦甲天下。”徽商崛起于草根,在创业之初,必然离不开勤俭节约,这样才能积少成多,由小到大,积累起原始资本;即使经商发家之后,依然讲求“家居务为俭约,大富之家,日食不过一脔,贫者盂饭盘蔬而已”。徽商和晋商一样,都是农业时代的传统商人,崇尚“以末致财,用本守之”。经商致富之后,不是置地就是盖房,积累起来的财富往往都变成可见的土地和建筑,不是“田连阡陌,富甲一方”,就是“堂构田园,大异往者”;有的竟至“田地万亩,牛羊犬马称是,家奴数十指”。因为受儒家文化的长期浸染,徽商将大量的资金用来修建会馆、义庄、祠堂和祖坟,置买族田,此外还要修订家谱,开办义学、试馆,兴建藏书楼等。从好处说,这种观念有慈善和反哺乡梓的一面;从坏处说,过度的挥霍和乐善好施也消耗了资本,损害了“扩大再生产”。对今天的人们来说,徽商已经成为历史,但他们的遗产仍处处可见,如著名的徽派建筑和江南园林,如被称为“国粹”的京剧。徽商赋予徽派建筑富贵及高雅的独特气质。行走在古老的徽州,但见“粉墙矗矗,鸳瓦鳞鳞,棹楔峥嵘,鸱吻耸拔,宛如城郭,殊足观也”。可以想象,当年就是这样一片山清水秀、人杰地灵的地方,孕育了引领中国商业数百年的徽州商人。徽州建筑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居住文化,徽州的“三雕”——木雕、石雕和砖雕尤为传神。每一处楼阁、门坊、廊柱、梁架、栏杆、窗户,都精雕细刻;主题多样,含义隽永,或神话传说,或名人典故,或奇珍异兽,或风景山水,或市井百态,或田园牧歌。这一切都让人浮想联翩,不禁感慨所谓“诗意的栖居”。美国史学家白铃安曾花巨资买下黄村的古老建筑荫余堂,漂洋过海搬到波士顿,被搬到美国的零件包括个木构件、块石片和当时摆放在屋内的生活用品。汤显祖曾说过:“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徽派民居以高深的天井为中心形成的内向合院,四周高墙围护,雨天落下的雨水,从四面屋顶流入天井,俗称“四水归堂”,这也形象地反映了徽商“肥水不流外人田”的心态。错落有致的马头墙又是徽派整个建筑的点睛之笔;不仅造型精美,更融合了古人的智慧。传统民居多是木质结构,村落聚居,最怕失火;在遭遇火灾时,马头墙便是防火墙,可阻断火势的蔓延。因为徽州地处偏远,大量白墙黛瓦马头墙的明清建筑保留至今,依然完好无损。特别是徽州的牌坊群,几乎为全国所仅见。著名的许国牌坊规模宏大,两座建筑,前为三间四柱三楼,后为两侧单间双柱三楼,所用石料质地精良,且巨大无朋,梁枋、栏板和斗拱上都有各种精美的立体雕塑,极其罕见。徽州之外,徽商还在江南地区留下大量鬼斧神工的私家园林,今天大都成为让人流连忘返的旅游胜地。或许有人不知道,京剧与徽商也有一段渊源。在徽商的会馆文化中,戏曲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实力雄厚的徽商拥有许多戏班,一般以昆曲和皮黄为主要戏曲样式。作为一个显赫的精英阶层,徽商的审美偏好影响了整个社会,戏曲行里的“徽班”风靡一时,有所谓“无徽不成班”之说。徽商可“布衣交天子”,徽班也连带着受到了皇帝的青睐。乾隆五十五年(年),乾隆皇帝八十大寿,徽商江鹤亭在扬州组织了一个徽班进京祝寿,没想到一下子轰动京城。这样一来,又有三家有名的“徽班”也去了北京,这就是著名的“四大徽班进京”。徽班很快成为北京戏曲舞台炙手可热的主角,“戏庄演剧必‘徽班’。戏园之大者,如‘广德楼’‘广和楼’‘三庆园’‘庆乐园’,亦必以‘徽班’为主。下此则‘徽班’‘小班’‘西班’,相杂适均矣。”此后,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发展革新,最后诞生了中国戏曲文化的最高成就——京剧。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上一篇文章: 有黑头可别乱挤,3个小妙招让黑头不复发,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
转载请注明:http://www.ohhayoungchina.com/htyf/1612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