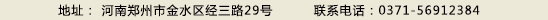原创新平回家
人,这一辈子。任何地方都可以佯装观光客的身份显耀都市浮燥得恶心的虚伪,唯独家不可以,任何人都没有资格。世上再硬翅膀飞不过家的高空;再大的脚步也跨越不了那份沉甸甸的养育之情。因为,家是世上最善良的一道门槛,永远为从这扇不起眼的门槛起程的孩子敞开,牵挂。无论你走多远、官多大,拥有万贯家财,还是沦落成人人唾弃的阶下囚。或是,全世界的家门都关上,但这道门里的那堆火塘永远期盼温暖你受寒的躯体而不灭。
谋生于都市灯红酒绿的檐下,回家的理由非常简单。前人就有“异鸟巢南枝”的感慨,更何况一日三餐的温饱还须靠人家苛刻的眼球宽容。回家,便成了我受伤时疗伤的泊岸。显然,一次次回到贫瘠的村庄,并非厌倦了都市咖啡的浪漫,去寻找城里人所谓的民风淳朴,更不是背上大包小包去探索发现存活于大山深处的传奇故事。
对于家,我绝对不想娇滴滴地出卖一道贫苦,奢望上天可怜我的同胞,更不相信缩命是绝对的定格。而面对现实,我能做的只是苦吟或是高歌。我怀疑,母亲还不算太老的脸庞生出过多层层叠叠的皱纹,难道是路过山寨的风雨造成的吗?
深夜/星星在天上聚会/她还在忙碌/一盏油灯陪伴/眨着微弱的光/夜和灯光一道/疲惫不堪/渐渐地/母亲的背影成了夜的影子/熬完一个夜/白发悄然萌芽/当她卷缩身躯入睡/再也无法醒来
透过忧悒的诗歌,灵魂在某个乡情遥不可及的角落疼痛得无法呼吸。这时,我分明看见了家的模样;看见了深居山林雕琢大山的母族。世间的事,幻不可测。对于像我这样混沌初开就试图摆脱山里的生存环境,用一身的稚气接受强大的物质冲击和文化影响。同时,身陷更加残酷的生存环境挑战前途未卜的人生,足以迷失生为何意?家为何物?
严格地说,像我一样由于不甘示弱而走出村庄的青年比比皆是,但让我时常怀疑他们对家的理解概念。大街上披着一身的洋装,头发原本黑得充满诱惑却偏要花钱把它弄得仿佛顶着一蓬枯草。上街遇到同胞害怕对方用哈尼语跟他(她)交谈,认为在大城市里有失个人的“尊严”,害怕露了所谓的“家底”低人一等,更有人害怕承认自己的民族属性和家居何处。同胞走进城里的家不会脱鞋子,媳妇的眼睛像刚被传染上眼疾病,看东西不顺眼,看人更不顺眼。于是,有人背叛事实,出卖母族。同胞间开始出售阴阳怪调的语言,出售别扭得寒酸到恶心的语言。当然,我指的是某些机关里的官员、职员以及形形色色走出哈尼山寨的讨生者。同胞啊!投胎于何族并没有我们个人的过错,存在的只是立命于何族的区别。假如心存一点点良知的话,把手放在胸口问问自己,什么叫血性?母亲十月怀胎后你血腥坠落的衣胞埋在哪个山头?
当然,如此追问下去实属无聊。但有一点必须承认,甚至到死亡。是一群半山腰上含辛茹苦挖梯田的乡亲把你拉扯长大;是门槛正对大山的家门收留了你。
记忆是揪心缠痛的。
作为六、七十年代哈尼山寨出生或者说有一点闯劲而离开村庄的同胞,如果血脉里还保持着一点母血的话,就应该知道贫穷是什么滋味;就应该明白口袋里揣着几片苦荞粑粑当做一个星期的口粮上学是什么感受;宿舍里买不起棉被而三、两个挤在一起过冬是什么心情。其实,这就是贫穷的味道。一个民族的历史基本上浸透了这种苦涩。尽管世态变迁,背叛昨天就是背叛了当初离家出走时的那道门槛,那群朴实的乡亲。我想,我是过份地展览了一个民族的苦难,尽管只表达了其中。当然,也应该是内心的一种驱使吧!因为站在如今各民族大发展的角度谈论民族问题,稍不注意,便意味着渲染民族分裂的思想,或者扮演救世主之类的角色,更何况我一个“居人篱下”的游子也没有这等能力。
如果说,回家的概念简单到只是过过年,跟人们凑凑热闹,或是家里有事必须回家了理才硬着头皮回家。那么,我愚昧地认为,人生正如只剩躯壳而无法谈论灵魂。
在我看来,作为一名哈尼族的子孙都应该为之幸庆。世界上很少有我们座落在大山深处的那道家门值得留恋的了。象征埃及古文明的金字塔,兴许是皇室帝王用刀枪威逼民众,靠人民的血肉之躯堆积而成。然而,梯田,没有刀光剑影的威逼。是我们的祖先为了生存,用巴掌大的锄头开拓出世人眼中可以与诸如金字塔、长城相提并论的造像,这足以让每一个哈尼人深感荣耀。谁如果没有深刻地了解我们的祖先从遥远美丽的诺玛阿美迁徙到茫茫哀牢群山的尘途;真正解读梯田博大精深的内涵。谁就没有资格谈论一名哈尼赤子一次简简单单回家的意义。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满腔热血,更不认为随便能划几行下三流的文字就有足够的资本谈论哈尼族或是哈尼梯田,但我至少深感荣耀,每次回到大山深处的村庄,都是一次亲情牵引灵魂回归故地的朝圣。
不厌其烦地回家,除了躯体躺在淳朴得掉渣的村庄,灵魂重复着解读同一个梦——
一群黑衣黑裤黑头帕的老者/我的祖先/跟着太阳的脚步/踩着月亮的影子/从一个山头爬到另一个山头/从河的北岸淌到河的南岸/是山收留了他们/山脊梁上挖田/挖好一丘/倒下无数个生命/不朽的尸骨埋在山上/梯田成了回家的路
一辈辈,一代代,爬山而活爬山而死的哈尼族。如今,尽管母亲忧郁的叫魂声千万次的呐喊;尽管山梁上敞开着多少游子最初启程的一扇扇家门。但真正能够把回家当做一种责任的人越来越少。
年8月25日,得知母亲放下手中的锄头,躺在她从来不愿彻底放平身腰的木床上。我迫不及待地赶回家,直到凌晨三、四点走了十多公里山路才回到母亲身边。尽管如此,除了一颗血淋淋的心之外,泪水便是唯一能和母亲交流的语言。然而,我终将明白,泪水浸湿不了母亲重于泰山的养育之恩。
家在哀牢山上,回家是我与生俱来的本能。不管身在何方,我都驻足一生的情感时刻注视着屋顶那一缕袅袅拔节的炊烟。时光荏苒,我把一生的精力凝结成都市檐下一个经不起风雨侵袭的小家,爱人经常把我日思夜梦却远在深山的家叫做老家。
是啊!
父母老去。
老家老去。
不老的只剩游子心中那份永恒的眷恋。
来源:梯田深处的耕者
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赞赏
转载请注明:http://www.ohhayoungchina.com/htyf/8506.html